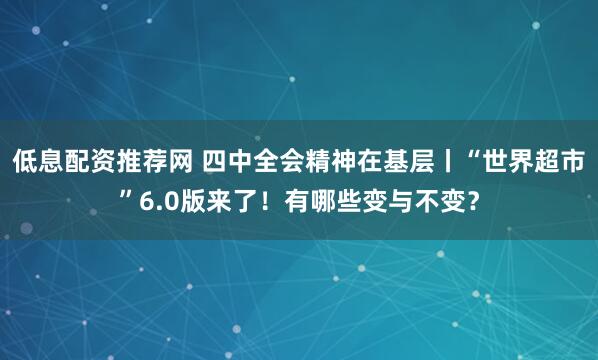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深夜,北平西长安街的司令部灯火未熄。电话铃声突兀响起,值班军官只说了一句“是新保安来的急电”,随即把听筒递给正在案前踱步的。短短三分钟低息配资推荐网,听筒那头的哽咽与枪声描述,将留在晋北防线的最后结局原原本本塞进了这位第二十一兵团总司令的耳朵里:战败、自戕、身边只剩一名警卫。
郭景云是傅作义三十年从戎生涯里最信任的师长,能打也肯打,被称“傅家军左膀”。此人一倒,平津战场的天平肉眼可见地倾向解放军。更糟的是,新保安的覆灭意味着绥远、察哈尔的外线防护扫地而空,北平外围再无成建制兵团可以机动支援。
军情简报摊在案头,光线下那一行鲜红批注——“第二线已失联”——让房间的空气都变得沉重。傅作义的心先是一沉,然后猛地抽紧。外人以为他素来沉稳,可责无可推这一刻也让他呼吸不畅。焦躁之余,他想起了两个字:和谈。只是,真走那一步需要有人点灯,照亮通往对岸的安全通道。

几乎同一时刻,刘厚同走进司令部。老先生穿一件旧棉袍,举手投足仍带着师范时期的儒雅味道。早年他是傅作义在绥远讲武堂的教官,学生见了老师,下意识还是要起身敬礼。刘厚同没有寒暄,先把一封印着“华北人民政府”红戳的公开信放桌上,随后斟字酌句:“局势已定,蒋介石正找末班替罪羊,作义公不可再犹疑。”这句话像从冷水桶里捞出的石头,砸在傅作义心口。
有意思的是,老先生并未苦口婆心,而是从万里之外的重庆说起。他分析,蒋介石此刻嘴上让傅作义“坚守北平”,心里却盘算着如何拖延时间,把华北主力抽回江南。换言之,北平一旦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城内守军成了可弃的棋子。不得不说,这番拆局让傅作义心里破开了一个小口子,冰缝透出几丝热气。
凌晨一点,刘厚同离开。走廊里残灯忽明忽暗,傅作义脑子里是嗡嗡作响的炮声和老师那句“新的政治生命”。他坐回桌前,手指摩挲收发电机的黑色开关,许久才下决心拨了个内部长途:“把冬菊的电话接进来。”
“赶快回来见我。”电话里他只说这七个字。
傅冬菊当时正在辅仁大学宿舍,小桌上摆着成堆宣传材料和一张李富春在《人民日报》上的演讲速记。她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春青”,组里交待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父亲进行劝导。可是父女多年未谈军国大事,她也忧虑该怎样开口。电话挂断,夜风从破窗灌进来,吹得墙角的油灯噗噗直响。她匆匆抓起一摞资料塞进挎包,赶往西长安街。
天刚蒙蒙亮,进门便把那份速记和几张油印小册子放在父亲办公桌显眼位置。傅作义抬眼,却没有多看纸张,只盯着女儿的脸。沉默像浓雾在屋里打旋,最终被一句直白的话剖开:“你是共产党员吗?”语言扑面,仿佛要把一切遮掩都挑破。
“还不够格。”傅冬菊的回答平静,却隐藏锋芒。简单五个字既避免正面承认,又留足父亲自己思考的空间。傅作义的眉头稍皱,随即舒展开来。他忽然懂了:家里这位小女儿,是真把北平的明天看得比自己的仕途更重。
接下来,傅作义打开抽屉,拿出一份拟好的“北平和平谈判设想”。措辞严谨,逻辑清晰:先确保城内三百万百姓安全,再移交军政权力,最后保留北京城的历史古迹与物资仓储。讲到“如何联系延安方面”时,他语速放缓:“能否通过你,直接把我这一意愿传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手里?”
父女二人对视。窗外冬阳升起,灰白城墙被染上淡金。试想一下,此刻的北平街头仍有人推着棉花糖小车,小贩吆喝声与远处炮声交织在一起。和平与战争的分界线,就悬在这间屋子的对答之间。
傅冬菊当即点头,提出先见到李克农,再由李克农安排北平地下交通线。傅作义对此方案几乎没有犹豫,他亲自提笔写信,直陈“三条基本意向”:停战、保护文物、妥善安置旧部。落款不仅有他的手签,还有私章“作义”。这一枚私章过去多用于发兵令,如今却被盖在递往解放区的密件上,历史的转折往往就隐藏在这种细节里。

不得不承认,傅作义对蒋介石仍存最后一丝疑虑。他让参谋以秘密电文向南京请示,询问能否抽调第二兵团北上救援。南京回电只有十六个字:“东线吃紧,无兵可拨,各自凭机,力求自保。”一看这行字,他再无侥幸。
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和平谈判的暗线铺设完成。刘厚同成了往返北平与丰台之间的信使,傅冬菊则负责将父亲口信准确捎至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所。四面围城的态势如同巨掌收拢,而交火却在奇妙的克制中暂停。城外解放军停止炮击,城内傅作义亦下令不得再开远程火炮。一道默契的静默线,不声不响画在史书正中央。
期间,有人劝傅作义“杀出重围”,去台湾或越南另谋出路。他没答话,只是翻看报纸角落一条消息:淮海大捷。那一刻,他心里的最后防线轰然坍塌。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和平协议正式签署。郭景云的遗照被摆在军部一角,黑白相纸里这位师长仍穿戎装、双目炯炯。有人说若他没自杀,或许北平守军还会挣扎更久。可是,真正让城门免遭炮火的,却是傅作义在女儿与老师双重劝导下做出的转向。

战争结束后,傅冬菊将“春青”身份转为公开干部,投身北京的城市接管;傅作义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来还参加了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历史对他们的评判各有侧重,但那一夜父女低声商量的情景,从此镌入一座古城的年轮。
值得一提的是,北平和平解放当天,全城仅有三起轻微冲突,六十多万国民党部队交械,有序列队出城。城墙、古建、校舍、档案完整无损,三百万市民照常上街买菜。郭景云虽未见到这一幕,然而他的死反射出的军心崩塌,却促成了城门内外的静音。历史的戏剧性往往如此:一声枪响,换来万籁俱寂。
2
华利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低息配资推荐网 富士康计划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投资17亿美元
- 下一篇:没有了